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许悦
近日界面新闻综合社交媒体搜索发现,近期多个商业地产博主发文称,LVMH集团旗下品牌路易威登和迪奥即将进入上海兴业太古汇,其中前者将开设面积接近千平但租期数年的临时门店。而在2024年12月,路易威登曾在兴业太古汇为重启的村上隆合作系列围挡巨幅广告。
界面新闻就此事向兴业太古汇方面求证,对方回应表示,商场品牌调改进程逐步推进,一层奢侈品牌调整仍处于进程中,未来将分阶段对外披露更多信息。
但兴业太古汇无疑希望头部奢侈品牌进入,巴黎世家此前已经在此开设一家中国旗舰店。
在财报里,兴业太古汇2024年的零售额同比下滑13.9%,93%的租用率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零售项目中的最低值。太古地产为此在财报里表示,这与商场的调改升级工程有关。
另外两个也在推进改造的项目分别是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和成都太古里,二者的零售额分别下滑0.2%和14%,租用率为98%和96%。广州太古汇和上海前滩太古里的零售额录得10.7%的跌幅和3.4%的增长。

这不是个例。
同样在多个城市运营高端商场的恒隆地产则表现更糟。2024年,上海恒隆广场和上海港汇恒隆广场的收入分别下跌6%和3%。武汉恒隆广场和沈阳市府恒隆广场的跌幅分别为16%和19%,后者在2024年秋季失去了香奈儿。
运营成都IFS和长沙IFS的九龙仓集团在2024年上半年收入同比下滑14%,包括商场和写字楼的投资物业收入下跌5%。但从2023年起,九龙仓集团不再通过业绩报告对外披露中国内地项目的出租率与租金情况。
但这并不妨碍这些高端商场继续在推动调改进程。

在已经推进调改的商场里,提升定位是共同目的。
三里屯太古里和兴业太古汇的聚焦点均是引入一线、二线奢侈品牌,这两个项目过去不以销售奢侈品见长。目前路易威登、迪奥和蒂芙尼已经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围挡装修,圣罗兰注册了一家新店,而Burberry的旗舰店已经在2024年秋季开业。
品牌入驻装修意味着租赁合约生效,由于北区未营业商铺面积比2023年同期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三里屯太古里的整体零售额。但三里屯太古里南区的调整基本完成,加入了始祖鸟、萨洛蒙等中高端运动品牌和Acne Studios以及Ami等设计师品牌。
这减缓了零售额下滑的幅度。
而兴业太古汇则亟需先有具有号召力的奢侈品牌入驻。它同样经历调整,但仍有多个空铺尚未围挡。这些铺位无法带来租金,不仅难以带来消费活动,并且也会影响整体形象和后期招商。
这解释了它为何会在品牌尚未入驻的前提下,会让诸如路易威登、范思哲以及Celine和Fendi等品牌挂上巨幅广告——这也是一种树立影响力并塑造形象的举措。
若其最终接受路易威登以临时门店的形式入驻也不意外,一个头部奢侈品牌“限时”现身能带来的号召力比数个二线品牌长期设店更强。除此之外,纪梵希和LOEWE、Max Mara等二线奢侈品牌已经开业。

对于那些已经存有奢侈品业态的项目,如今的核心是推动业态多元化。
作为西南中心城市,成都虽然虹吸周边奢侈品消费,但实际体量仍不如能容纳多个高端项目的北京和上海。随着全球奢侈品行业遇冷以及成都SKP的开业,本已有成都IFS作为竞争对手的成都太古里,其客源无可避免地会遭受二次分流。
而成都IFS和成都SKP均强目的性消费为特点的商场,前者目前的调改逻辑是为路易威登和香奈儿等头部奢侈品牌提供更大的零售面积,而后者的品牌数量和层次更全,带来了The Row等小型设计师品牌的西南首店。
基于此,成都太古里的调改思路虽然也是开设旗舰店,但涵盖了更多体验,覆盖的价格带也更广。在路易威登于2022年开设餐厅后,迪奥近期也在新开设的旗舰店里设置咖啡店。运动品牌数量也在增多,Wilson西南旗舰店内置了咖啡厅,阿迪达斯品牌中心则带来了提供交互体验的创意实验室。
随着户外运动热潮高涨,越来越多高端商场开始放大运动品牌占比。
从开年至今,港汇恒隆广场引入了户外羊毛衫品牌Icebreaker、特步集团旗下网球品牌Kswiss、户外露营品牌牧高笛,而已经开业的户外运动品牌包括始祖鸟、迪桑特、凯乐石和猛犸象等。目前商场的运动品牌总数超过20个
上海静安嘉里中心也是如此,其近期引入了诸如Goldwin和Vuori等品牌的上海首店,On、Peak Performance和Hoka One One等新兴户外品牌则早已入驻。目前商场的运动品牌总数约为20个,分布在地下一层、一层和三层。

或许是感受到了市场变化的趋势,在南京西路上以重奢为核心的上海恒隆广场也开始调改。
受到商场体量限制,只有少数头部奢侈品牌能够开设融合多种业态的跨层旗舰店,但恒隆仍将三层原香港买手店Joyce的空铺重新分配,交由Alexander Wang、Sacai、Isabel Marant以及鬼冢虎的Nippon Made支线和香氛品牌潘海利根开店。
很显然,除了维持重奢的基因,上海恒隆广场显然也想丰富现有的生活方式氛围。
但当恒隆广场这样的地标性高端商场向更多类型的品牌“开放权限”,周边以设计师品牌为主打的芮欧百货最先受到冲击。Sacai便是从芮欧专场到了恒隆,Stella McCartney也在恒隆店开业一年后关闭芮欧门店。
事实上,伴随着全球奢侈品消费遇冷的趋势,能够在同城开设多家门店的奢侈品牌数量正在减少。芮欧百货属于最先受到冲击的对象,除了设计师品牌流失,位于一层的纪梵希和Moncler也选择关店,后者转移到了港汇恒隆广场。
除了继续在二楼以上引入更多独立设计师品牌之外,目前尚未看到芮欧百货有推出应对一层奢侈品牌撤离的策略。类似的还有武汉恒隆广场和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奢侈品牌撤离留下了大量空铺,但至今没有积极对其进行招商填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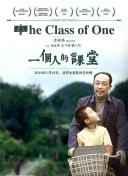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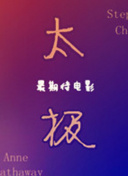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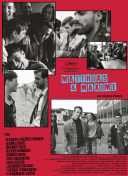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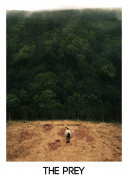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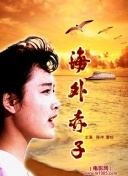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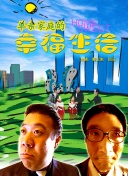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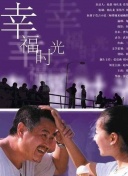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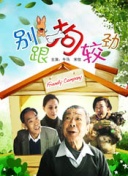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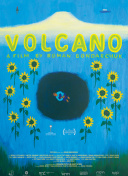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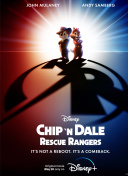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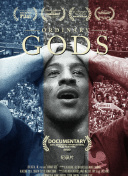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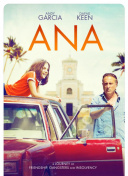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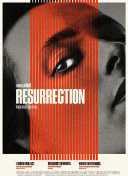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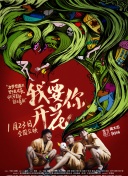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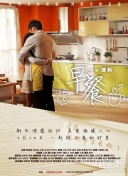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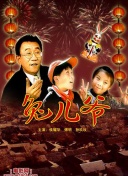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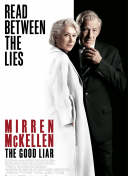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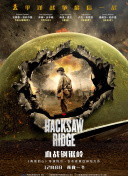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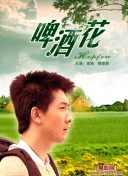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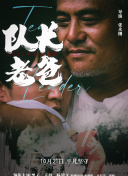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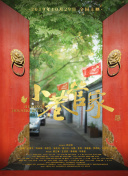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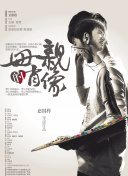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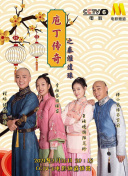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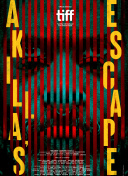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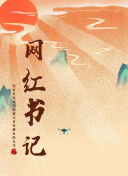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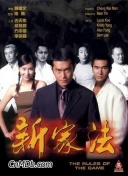
 48158
48158 46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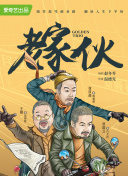

 18095
180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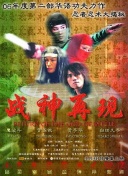 59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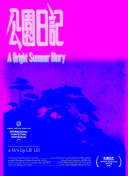 76276
76276 17
17


 65573
655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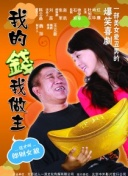 36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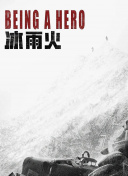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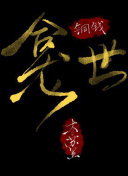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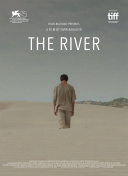 63128
63128 4
4


 86478
86478 85
85


 30367
30367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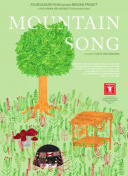
 63524
63524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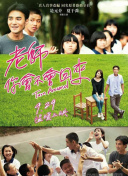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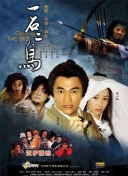 62738
6273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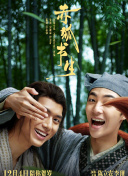 4
4


 31856
31856 47
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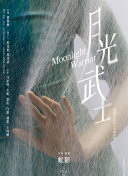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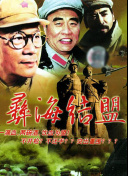

 71272
71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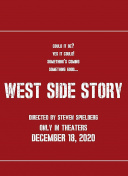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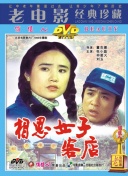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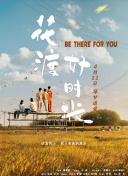 99712
99712 97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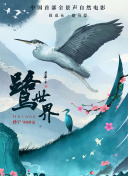 54978
54978 31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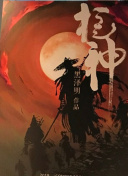

 63720
6372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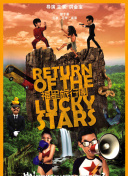 90
9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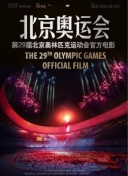


 94331
94331 53
5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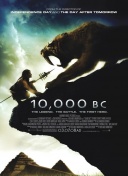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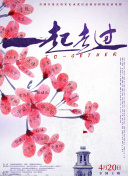

 29063
29063 54
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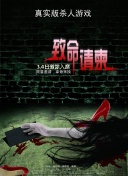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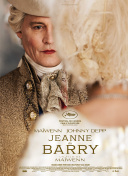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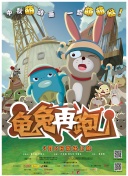 68942
68942 21
21


 89181
89181 94
94


 23218
23218 58
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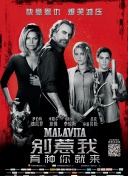


 28745
28745 52
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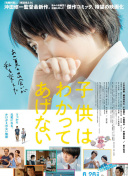


 81201
81201 44
4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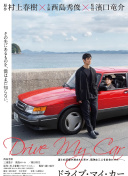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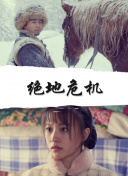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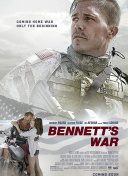 17480
1748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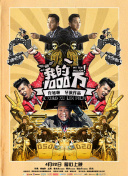 70
70


 89028
89028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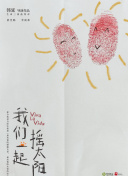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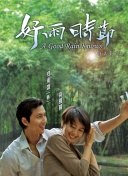 98746
98746 88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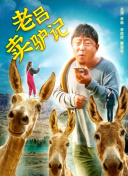

 79267
79267 68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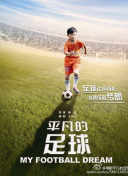

 83517
835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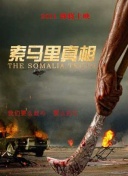 81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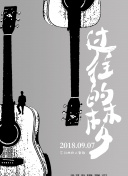 27017
27017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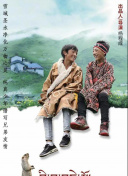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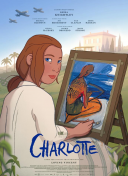 54410
54410 77
7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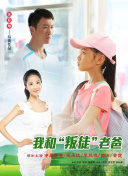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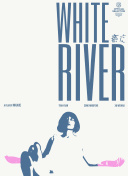

 62398
623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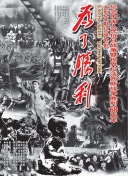 1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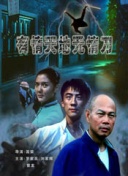


 63428
634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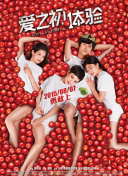 58
58


 63473
634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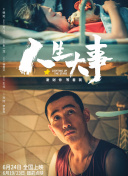 31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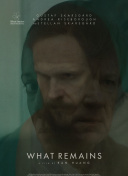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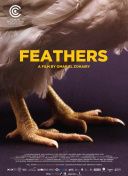 47199
4719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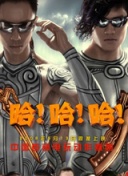 19
19


 84052
84052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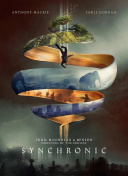 46245
46245 22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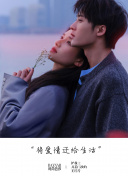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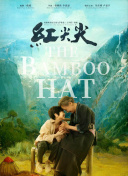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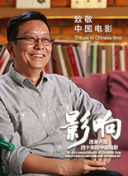 19684
19684 80
80


 22271
2227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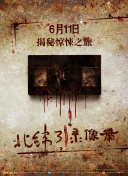 49
49


 94874
94874 50
50
 36152
36152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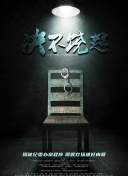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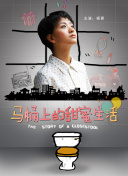 45060
45060 29
2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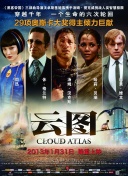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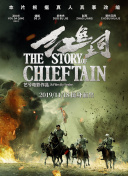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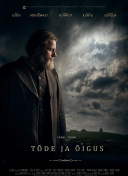 74946
749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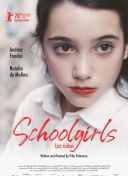 99
99


 90160
901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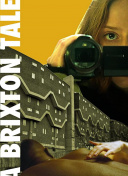 42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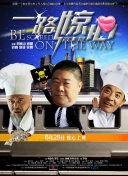 41857
4185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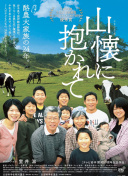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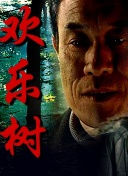 66369
66369 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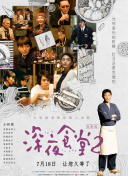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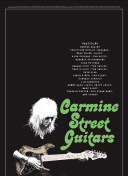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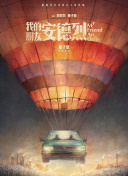 47534
47534 52
52


 61701
61701 41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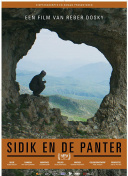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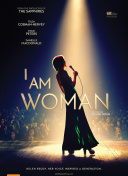 60
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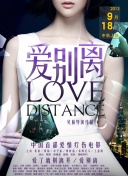


 68054
680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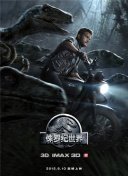 69
6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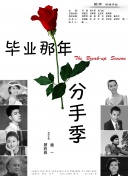

 93840
93840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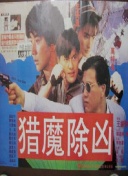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