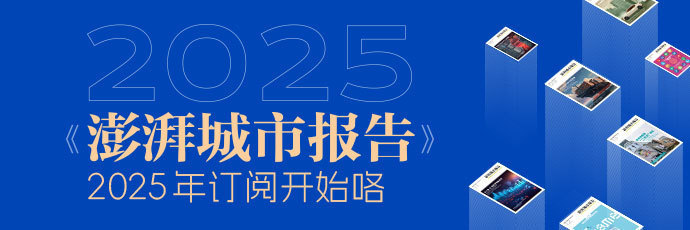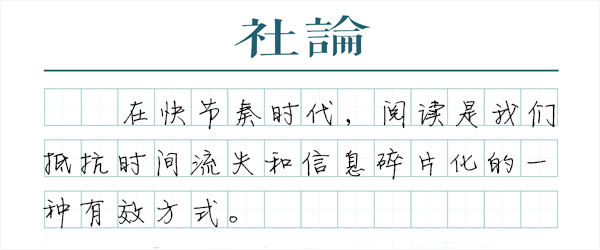有人有片资源吗在线观看WWW视频:可以做羞羞的事情的模拟器下载-上海农房翻建为何难?基层盼政策适度松动

城市更新热火朝天,郊区农房翻建也等不得了。
上海郊区部分村镇房屋破旧问题日益突出。房屋破旧,不仅有损风貌,还关乎市民居住安全和质量。特别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以下简称“农房”),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甚至生产的场所,也构塑了农村“风景线”。上海农房现状的成因是什么?村镇房屋翻建难在哪里?
2025年3月以来,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调研了上海郊区的奉贤区、浦东新区、嘉定区的7个行政村,并基于调研情况采访基层资深房屋管理人士,分析相关数据、政策——特别是《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上海16号令”)。
七成以上农房房龄超25年,翻建需求急迫
在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下,农村宅基地,指农村村民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享有的可以用于修建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一般来说,村民可以在原有宅基地房的基础上自行翻建、更新。随着改革开发以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翻建农房也成为农村居民提高居住生活的质量和安全度,并改善农村风貌的主要方式。
据统计,上海共有农村自建房近90万套。其中2000年以前建造(即房龄25年以上)的农房占比超过7成,而近15年建造的农房不到9%。
近期住建部已宣布将“2000年以前建成的城市老旧小区全部纳入城市更新改造范围”,并“鼓励居民自主更新改造”。在上海农村,2000年以前建造的农房占比高达73.7%。此类“老旧”农房不仅建造时间较长,更重要的是由于早期建筑工艺的局限,大都采用预制板砖混结构,房屋质量、安全和使用寿命略逊于当前更常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我们一到台风季节、汛期雨季很担心的,特别去年台风天,房子都是要像倒塌一样的,就怕房子吹垮了,压下来砸到人了,这边离海又更近……非常担忧住在里面的居民。人家想建又没有通道。(只能)赶紧转移一些居民到村委会、居委会……”浦东新区大团镇三墩居委书记吴华娟对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吐苦水”。这并非孤例。
可见,农房应该翻修,无论是从居民居住安全、质量,还是从总体风貌来说。同时,上海农村居民也有能力负担、有意愿翻建自家农房。在长三角城市中,上海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4年)排名第9名,落后于杭州(第5)、苏州(第7)、宁波(第4),却高于南京(第14)、温州(第21),温州(第10)等几个重要城市,靠近长三角第一梯队。基于统计局公开数据并经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测算,与上海城镇居民相比,近10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更多;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从2013年的2.34倍缩小至2024年的2.04倍。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所调研的各村村委,无一不倾诉有关农房翻建需求多、但“无通道”没法翻建的困惑。

2025年3月,嘉定区曹王村一处农房,该区域因河道拓宽工程将被拆迁。本文图片均为 周燕玲 摄

2025年3月,嘉定区曹王村一处正在建造的农房别墅,与上图农房仅一墙之隔。现场建筑工人说,在这块地被确认不被拆后,房主很快积极翻建。
政策变化导致农房翻建难
农房日显老旧,翻建需求日增,但为什么近年农房翻建数量却很少呢?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审批政策。农村居民希望翻建宅基地上房屋,但是,未经审批擅自翻建重盖的属于违法违规行为。
调研发现,近年上海农村宅基地自建房面临更严格的规范、限制,已在基层出现许多张力。特别是2019年新的《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简称“上海16号令”)出台(替换老办法,即2007年71号令),对上海农村自建房产生了重大影响。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通过访谈部分基层规建工作人员和农村村委人员,并对比上海16号令和71号令,发现政策上的三点变化可能是造成了农房翻建难的客观结果。
第一个变化,规划先行,大多数农房“不能”翻建。
16号令强调,农村自建房不仅要符合宅基地用地性质,还必须符合且基于规划。其第六条新增规定:翻建、改建住房前提是“位于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范围内”(业内常称为“规划保留区”),而在此范围外即“规划非保留区”的农户只能选择“上楼”或选点“集中建房”。
“规划先行”使大量农村自建房处于“除非危房,不得翻建”的处境。“规划”被视为农房翻建前提和刚性要求,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自身的完善、周全、确定性、合理性也应经得住挑战。仅从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调研的几个村镇来看,就发现存在几个有待商榷的疑问:
其一,不允许农房翻建的“规划非保留区”的农房数量多于“规划保留区”。
据上述基层资深房屋管理人士提供的数据,某镇大概有11,000多户宅基地自建房,其中约8000户在“规划非保留区”,而在8000户中至少有6000户建造于1990年之前,但不允许农房翻建,只能引导集中上楼、集中平移或拆迁。如果超7成的农房需要靠政府多级财政之力拆迁、修建集中居住完成住房安全和质量改善,这在各地财政吃紧,上海农民集中居住政策面临“转换”的背景下,是否可行呢?
其二,规划本身具有远期性、不确定性,却宰制、刚性地影响了农村实际生活。
部分农房属于“规划非保留区”,即便有规划,也是在10年以后,或者规划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但也不能翻建,甚至一些基础设施更新、乡村振兴项目“也不可能再来投钱”;部分农房所在区域还可能因为“规范没落地”,暂时没有规划,因而也不能审批农房翻建。
还有些村,因为全镇集体土地因“以土地换保障”政策已被政府代征,即便还未正式征收、改换土地性质,农村村民也不能翻建宅基地房。
第二个改变是,资格收紧、用地上限降低,申请人“不愿”改建。
首先,建房用地人的资格要求趋严,部分农民或农村家庭成员失去了建房资格。相比71号令规定的村民资格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6号令增加了“具有本市农业户口”的要求。这一要求使得一些农村家庭,能够申请建房资格的人数减少,其被审定的翻建房面积数也相应缩小,从而使得一些农户“不愿/不敢”翻建。
例如上海市人大代表瞿磊就曾公开建议“赋予失地农民房屋翻建权限”,他指出,“上海的失地农民数量庞大”,“一部分因被征收承包经营地而转为非农户口性质的农民失去了建房资格”,而他们“生产、生活、居住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1]。他还举例:“以奉贤区南桥镇为例,现存宅基3700余户,除近千户采用集中上楼安置以外,剩余宅基地房龄大多在30年以上,农民改善人居环境愿望强烈。”
还有一些农村家庭成员,被新政策排除在申请资格之外,如“外来媳妇/女婿”。按上海户籍制度,外省市人员与具有本市家庭常住户口的居民结婚登记后,须等待10年(且35岁以上)才能在上海(配偶户口所在地)落户,因此在成为家庭成员10年之内,暂无上海户口。此类情形,以往可以按照“标准家庭户”进行核定、提前纳入的,只要证明“家庭成员接纳”,但新政策明确强调“具有本市农业户口”,无法如此操作。
其次,建房用地面积上限不断压低。从上海71号令到新的16号令,可用建房占地面积上限从200平方米下调至160平方米。
这被很多村民理解为,要改建旧房,审定后的一些房子会“变瘦”,从而也“不愿/不敢”翻建。当前农村自建房多为老人居住,他们偏好“接地气”,活动不便,居住活动多在一楼,不喜上楼。占地面积的缩减明显将降低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并且,农居不仅是生活场所,也常具备农业生产设施工具储放功能。
可见,村民并非真不愿翻建,所谓“不愿”“不敢”,只是在既有制度/政策下不得已的选择。
第三个变化是,程序繁琐,增加费用,拉高农房翻建成本。
上海16号令实施落地的过程,因强化了管理规范、线上报备等,导致落地时间和执行流程都客观上延长。
上述基层资深房屋管理人员透露,16号令作为市级文件2019年就下发,但很多区2021年才发布区级文件,而且还须发布镇级文件。这层层下达的几年时间内,都无法办理农房申请/审批程序。并且2022年开始,农房审批在原有线下基础上加入线上流程,线上线下同步,更拉长了办理时间。同时,农房建设审批流程中,参与部门更多了,从之前以规建口为主,改为部分环节需要农委、规资、建交其下若干条线“联审”。程序上更严谨,但同时也变得繁琐。
某不愿具名的村干部因遭受村民的诸多压力和责难,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吐槽:“三年多了政策是否落地都不知道。(申请)翻建房屋流程、时间很长,就算是可批准的。我现在碰到一个两年前申报翻建(的农户),到现在还没有审批通过。”
此外,新政下,鉴于流程规范化和房屋质量管控等的需要,农房翻修申请过程还产生了一定费用,比如用于购买用地测绘、定界报告与施工图纸服务。
2024年4月,中央多部分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重申,对农房实施改扩建,应当依法办理用地、规划建设等有关审批手续,严格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
农房建设确实需要规划和规则,各级政府建立规范、规则,甚至“规划先行”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各地执行和实施过程中,这些规划、政策会如何影响当地农村、农民的实际生活,是否会产生非预期的政策后果,甚至是否真的有利于达成政策目标,需要纳入观察和考量,形成上下互动并考虑做一定优化调整。
4月16日,上海召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提到,“要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大力解决农民居住困难,实事求是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品质”。
适度放开房屋翻建的“通道”,在可行的引导和规范下,不难想象,上海将在短期内以较少的投入,改变农村的房屋风貌及人居环境。
-----
城市因集聚而诞生。
一座城市的公共政策、人居环境、习俗风气塑造了市民生活的底色。
澎湃城市观察,聚焦公共政策,回应公众关切,探讨城市议题。